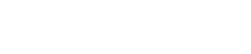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商业贿赂条款是否大而美?——对比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镜像立法的思考和启示
发布时间:2025-09-12
文 | 潘志成 李庆庆 汇业律师事务所
许多人有追求完美的良好愿望和冲动,立法也是如此。将规制受贿行为的条款放入规制不正当竞争商业贿赂条款的体系,虽然条款形式更加完整,但其解释必然也受到体系的影响和限制。然而,对受贿行为的执法,存在“破坏竞争秩序”、“利益出卖和交换关系”、以及“违反职务廉洁性”三种不同尺度。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商业贿赂条款中对受贿行为的禁止,究竟应按何种尺度执法?这里不仅涉及对法律条款的理解和适用,也涉及企业合规的界限。本文尝试通过将合并立法模式和单独立法模式进行比较,揭示其中的问题,并探讨执法权限与企业合规的合理限度。
一、走向大而美的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商业贿赂条款
2025年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新《反法》”)再次修订。其中,反商业贿赂条款的一处重要修改是增加了对受贿行为的禁止性限制。修订后的新《反法》第8条第2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收受贿赂。”同时第24条规定:“有关单位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贿赂他人或者收受贿赂的,由监督检查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吊销营业执照。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实施贿赂负有个人责任,以及有关个人收受贿赂的,由监督检查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新《反法》反商业贿赂条款增加了对受贿行为的禁止性规定之后,改变了原法条仅禁止行贿行为的单向做法。在条款中同时禁止行贿行为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受贿行为,这种镜像立法使得反商业贿赂条款从逻辑和形式上更加完整。然而,内容增加、条款增大是否必然使得条款更加完美?大而美的反商业贿赂条款是否会影响法律的实施和适用?
无独有偶,美国于2023年底颁布的《反外国官员索贿法案》(Foreign Extortion Prevention Act,以下简称“FEPA法案”),该法案也被解读为对《反海外腐败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以下简称“FCPA法案”)的镜像立法,弥补了后者仅禁止行贿行为的单向性,增加了对海外官员受贿、索贿行为的禁止。然而,FEPA法案却并不是对FCPA法案条款的修订,其先是在美国法典汇编第18编(犯罪及刑事诉讼程序编)第201条,即联邦政府官员受贿条款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之后又从该第201条中删除,演变为独立的第18编第1352条。FEPA法案立法体例的选择和演变,揭示出立法机关考量到禁止受贿索贿行为与禁止企业行贿行为在立法目的、执法机制和执法权限等方面存在差异,放入同一条款之中可能会导致法律体系发生内在冲突,并可能导致在理解和适用时发生偏差。
二、FEPA法案立法演变
FCPA法案与我国原反商业贿赂条款比较类似,仅单向禁止行贿行为。FCPA法案禁止证券发行人、国内主体、及在美国境内或利用美国邮件等州际间贸易设施的三类主体通过向海外政府官员或雇员行贿,获得不法的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虽然FCPA法案禁止三类主体的行贿行为,但对于收受三类主体贿赂的政府官员或雇员,FCPA法案本身并未追究任何法律责任。
美国国会于2023年底颁布的FEPA法案,可谓FCPA法案的镜像立法,弥补了FCPA法案的空白。FEPA法案专门针对向前述FCPA法案的三类主体索取、收受贿赂的外国政府官员、雇员,包括政党官员、雇员,国际组织官员及雇员,以及任何代表政府、政党或国际组织的人士,规定其索取、收受、允诺收受贿赂的行为构成违法,将承担最高25万美元或贿赂额三倍的罚款,并/或承担最高15年的刑事责任。
可以看出,FEPA法案与FCPA法案形成了相互镜像对立的一组法律,二者不仅对行贿主体、受贿主体采用了相同的概念,而且对贿赂的构成也规定了相同的要件,例如不要求行贿行为与职权行为之间的先后顺序,但均要求交换关系(quid pro quo)。同时负责FCPA法案和FEPA法案执法的美国司法部刑事执法局欺诈犯罪处曾专门发布说明,指出其在依据FCPA法案执法时,将同时考虑针对外国政府官员适用FEPA法案执法。
然而,FEPA法案并非是在FCPA法案条款,也即美国法典汇编第15编(商业与贸易编)第78条等证券法相关条款基础上进行增补。FEPA法案首先是对适用于美国境内联邦政府官员受贿行为的美国法典汇编第18编第201条受贿条款基础上进行修改,在原第18编第201条款的基础上增补了(a)(4)(5)和(f)条款。后来在2024年7月,美国国会又对第18编第201条新增的条款进行了删除,将该条款作为独立的第18编第1352条,形成现在的第1352条(a)(b)两个条款。
FEPA法案的立法体例选择和演变,其背后的重要考量因素就是不同法案存在不同的立法目的和执法机制,放在同一体系中可能会存在解释和适用方面的冲突。例如,FCPA法案本身是基于美国证券法的条款发展而来,其立法目的是禁止以证券发行人为主的三类主体,通过行贿行为获得不法的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损害证券交易市场或其他证券交易参与者利益,因此可以由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违法者处以民事或行政责任;而外国官员索贿受贿行为,尽管也会间接影响证券交易市场或证券交易参与者,但该行为更直接损害的是外国政府,是一种损害职务廉洁性的行为,从逻辑上难以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外国政府官员进行民事或行政处罚,因此FEPA法案一开始就未选择对规范商业与交易行为的第15编第78条(FCPA条款)进行修改,而是选择对规范犯罪与刑事诉讼程序的第18编第201条(贿赂条款)进行修改,作为增补的第201(a)(4)(5)和(f)条。
同样,美国国会后来又考虑,第18编第201条更类似于禁止联邦政府官员受贿的总则条款,而FEPA法案涉及对海外其他政府官员索贿受贿行为的执法,其不仅自身存在执法上的特殊性,而且许多总则条款并不适合用于解释FEPA法案条款,将FEPA法案作为特殊法单独立法更为适合。例如第201(c)条禁止联邦政府官员因履行职务行为而接受酬谢,其并未要求交换关系(quid pro quo),而FEPA法案强调交换关系。因此将FEPA法案条款放入第201条,可能导致条款之间存在内在冲突。据此,FEPA法案又从第201条中脱离,成为单独的第1352条。
事实上,在美国的刑法体系中,针对不同类型主体受贿行为单独立法的情形并不罕见。例如针对联邦政府资金资助的地方政府以及教育和医疗机构官员及工作人员受贿行为的立法,也是作为第18编第666条单独立法。美国最高法院2024年审理的Snyder v. US 案就涉及第666条的理解和适用。在该案中,印第安纳州波特市前市长施耐德被指控在该市采购垃圾车的交易中帮助了卡车交易商,并事后收受了卡车交易商的款项,但施耐德认为该款项与采购垃圾车交易没有关系,而是对他提供顾问服务的感谢费用。该案争议焦点在于第666条是否禁止向官员支付不存在交换关系的酬谢,最高法院确认在适用第666条时,交换关系(quid pri quo)必须是受贿行为的构成要件,换言之,针对联邦政府资金资助的地方官员或工作人员,接受没有交换关系的酬谢并不构成违法。但是,该案判决仅限缩了对第666条的解释,并未影响第201条的解释和适用,对联邦政府资金资助项目之外的联邦政府官员因其履行职权进行感谢,即便没有交换关系,仍然可构成违法。
三、新《反法》中反商业贿赂条款增加镜像立法后仍需要明确的问题
同样是针对收受贿赂行为的镜像立法,FEPA法案选择了在FCPA法案和刑法受贿总则条款之外单独立法的路径,而中国的反商业贿赂条款已在形式上走向大而美的道路。尽管单独立法并非唯一可选择的路径,合并立法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但是,合并立法可能会带来的一些理解上的困惑和潜在冲突,仍然需要我们予以厘清和避免。同时还有一些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也有待执法机构在未来执法时进一步澄清。
1. 立法目的及适用前提
《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保护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权益。新《反法》第8条第1款禁止经营者通过给予财物或其他手段贿赂相关单位或个人,以获得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换言之,该条款禁止经营者通过不法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因此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目的。
然而,新《反法》第8条第2款禁止前款所规定的单位或个人收受贿赂,其立法目的和适用范围可能会与禁止行贿行为条款存在差异。收受贿赂不同于经营者行贿的行为,尽管该行为也会间接影响竞争秩序或其他经营者或消费者利益,但更为直接的是破坏了职务廉洁性,其为了贿赂而选择经营者的商品或服务,而不是基于公平的价格质量竞争作出选择,事实上出卖了雇主或委托方利益,无论其选择的商品或服务是否是质次价高的商品或服务,均具有可责性。
更进一步而言,如果立法者对政府官员或工作人员有特殊的职务廉洁性要求,甚至可以不要求收受财物是基于交换关系(quid pro quo),例如美国法典汇编第18编201条对联邦政府官员因履行职务行为接受酬谢的禁止。在实践中,我国许多大型企业也有类似廉洁公约,禁止工作人员接受经销商或交易相对方的任何礼品或宴请,无论经销商或交易相对方是否有谋求交易机会的目的。
事实上,新《反法》反商业贿赂条款对单位或个人收受贿赂的禁止,可能存在三种不同执法尺度和适用条件,分别是:1)破坏竞争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出卖雇主或委托方的不法利益交换行为;以及3)纯粹的违反职务廉洁性的行为。执法机关需要明确该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前提,究竟是对纯粹职务廉洁性的保护,还是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禁止。换言之,该条款适用是否需要行贿者具有牟取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的目的?是否需要收受财物的相关单位或个人与行贿者之间具有交换关系?是否对不具有交换关系的酬谢也完全禁止?
作为比对,FEPA法案并未选择通过修改FCPA法案进行立法,因此FCPA法案的条款和立法目的并不能直接用于解释或限制FEPA法案的适用。同时,FEPA法案即1352条(b)(5)款也明确规定,FEPA法案所规制的行为并非是FCPA法案项下违法行为的附属行为,违反FEPA法案并不以违反FCPA法案作为法律适用的前提。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FEPA法案的立法目的之一是保护美国企业,因此其对向美国企业或美国证券发行人收取、索要贿赂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长臂管辖执法。FEPA法案的立法目的并非要求外国官员具有廉洁性,其也不适用于外国政府官员向外国企业收取索要贿赂的行为。
2. 执法权限与法律责任
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构是市场监督局,其可对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同时,新《反法》在法律责任章节,明确了违反本法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经营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其他经营者针对破坏竞争秩序、损害自身合法权益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商业贿赂行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权益。
新《反法》针对收受贿赂的行为,在第24条规定了行政处罚责任。然而,收受贿赂方的行政处罚责任和刑事责任如何衔接?行政罚款和刑事罚金能否同时适用?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在实践中明确。我们理解,当存在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竞合的情况下,由于行政处罚和刑罚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责任,比如贿赂行为的行政处罚种类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罚款以及吊销营业执照,刑事责任则包括有期徒刑、拘役、罚金等责任,违法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然而,对于行政罚款和罚金,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5条第2款规定:“违法行为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行政机关已经给予当事人罚款的,应当折抵相应罚金;行政机关尚未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不再给予罚款。”
作为比对,FEPA法案的执法完全由美国司法部刑事执法局负责执法,法律责任仅包括针对个人的罚金和或有期徒刑,不存在类似FCPA法案项下的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追究的行政处罚责任。
3. 个人责任与企业责任
新《反法》中的反商业贿赂条款规定,员工个人的行贿行为,原则上企业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除非“经营者有证据证明该工作人员的行为与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无关。”
然而,对于个人收受贿赂的情形,该个人的单位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新《反法》第8条及第24条对此均未明确。我们理解,不应直接推定个人受贿时个人的单位应承担责任。针对行贿行为而言,经营者的工作人员在行贿时,实际上是为经营者谋取交易机会或者竞争优势,且实践中工作人员的行贿行为常常也受到经营者的指示或者同意,因此新《反法》第8条第4款直接推定经营者的工作人员进行贿赂的,应当认定为系经营者的行为,同时给予经营者推翻推定的机会。
然而,针对个人受贿行为,其目的是为了接受贿赂,而非为单位谋取任何利益,甚至可能出卖了雇主或受托方的利益,选择了质次价高的商品。从该角度来说不宜直接推定个人受贿时,其单位也应承担责任。
作为比对,FEPA法案则明确规定由违法者个人承担刑事责任,违法者个人行为并不会传导给其雇主或单位,使得雇主或单位承担法律责任。
四、结语
新《反法》已经正式颁布并即将开始实施,反商业贿赂条款选择的将行贿行为与受贿行为合并立法的模式已不可改变。然而在此既定模式下,我们仍然可以思考,条款更大内容更全的条款,如何才能在执法时真正实现立法目的?建议执法机构可以参考美国FEPA法案立法演变及其背后的考量因素,准确厘清收受贿赂行为与行贿行为的立法目的差异、以及对收受贿赂行为进行规制的执法限度,避免条款体系解释可能会给法律适用带来的不必要干扰,实现最佳执法效果。
*本篇文章首发于威科,感谢汇业亚特兰大分所温勇律师对美国法律检索研究给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