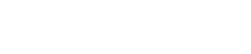香港信托相关法律的概念与应用
发布时间:2025-08-12
文丨陈少彬 汇业律师事务所 律师
近日,三名自称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子女的人士与现任董事长、宗庆后之女宗馥莉在杭州和香港的诉讼纠纷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诉讼中涉及的家族内幕和继承纷争也让信托这一工具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焦点,引发了公众对信托法律概念、成立条件及其应用的广泛讨论。作为一种来源于普通法系的灵活的财务管理工具,信托的法律框架不仅为资产保护提供了保障,也允许财富在不同代际间有效传承。本文将探讨香港信托相关法律的基本概念及其实际应用,以期为读者提供更全面的理解。
一、 信托的概念与由来
(一)信托的概念
对于大陆法系的法律从业者而言,普通法系下的信托制度并不像刑法、合同法那样能在大陆法系中找到直接对应的法律制度。事实上,即便在普通法系内部,信托也因其复杂性和多样性而难以被简单定义——它并非单一的法律概念,而是基于不同需求发展出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在普通法系中,Underhill教授提出的信托定义因其简明性和权威性被广泛援引:
“信托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义务,该义务要求受托人(trustee)为其可控制的信托财产(trust property)进行管理,以保障受益人(beneficiaries或cestuis que trust)的利益——受托人本身亦可作为受益人之一,且任何受益人均有权要求强制执行该义务。”[1]
此外,海牙公约也对信托的概念及特点进行了一些界定。海牙公约《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公约》第二条规定:
“为本公约目的,‘信托’这一术语是指财产授予人为了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将资产置于受托人的控制下而设立的法律关系,不论该关系是在财产授予人在世时或死亡时生效的。
信托具有下列特点:
(一) 该项财产为独立的资金,而且不属于受托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
(二) 信托资产是以受托人名义,或以代表受托人的另一个人的名义所持有;
(三) 受托人有权和有责任,按照信托的条款以及法律赋予他的特殊职责,管理、使用或者处理信托资产,并须对该等权力和责任负责。
财产授予人保留某些权利和权力以及受托人本身作为受益人可以享有权利的事实,并不一定与信托的存在相抵触。”
需注意的是,上述定义并不涵盖所有类型的信托。Underhill教授的定义主要指向明示私人信托(express private trust),而海牙公约的定义仅适用于“自愿设立并有书面证明的信托”。[2]根据不同划分标准,信托制度还可被分为多种其他类型的信托:
1. 根据设立方式划分:明示信托 (express trust)和默示信托 (implied trust)
明示信托是由财产授予人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设立的;默示信托是由于法律原则的运行而产生,或由具体的事实情况默示地产生。其中,归复信托 (resulting trust)和法律构定信托 (constructive trust)等则是默示信托中的常见类型,其具体特征与适用规则将在后文详述。
2. 根据受益人的类型划分:公共信托 (public trust)和私人信托 (private trust)
公共信托是指慈善目的的信托,一般要求该信托具有可确定的受益人,这样法庭才可得知应为何人的利益执行信托条款并命令受托人行使;私人信托是指为个人或私人公司设立的信托,一般是因为受益人和财产授予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产生的。
3. 根据受托人具有的自由裁量权划分:固定信托 (fixed trust)和全权信托 (discretionary trust)
在固定信托模式下,财产授予人对信托内容、资产分配等做了详细的规定,受托人几乎没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在全权信托默示下,受托人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可在一定范围内决定将信托资产分配给谁以及分配多少,但同时受托人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4. 根据受托人的责任划分:被动信托 (bare trust)和特别信托 (special trust)
在被动信托模式下,受托人除了持有信托资产并在将来将其转让给受益人外没有其他的责任;而特别信托中的受托人则负有许多其他责任,如投资、管理信托资产等责任。[3]
(二)信托的由来
普通法系的信托制度来源于中世纪的“用益权”(“use”)机制。这一机制早在1066年诺曼征服英格兰之前就已存在,允许财产以“ad opus”(意为“为……之利益”)方式转让给他人。[4]信托制度中“use”(用益权)这一术语的词源可追溯至诺曼法语“oes”,其词根则来自拉丁语“opus”(意为"利益"或"受益")。这一词源演变表明,“ad opus”在中世纪法律语境中专指“为特定主体之利益”的财产安排,与现代英语中“use”(使用)的日常含义存在本质区别。[5]
相传在公元11世纪左右,欧洲的领主、骑士等在教廷的鼓励下积极加入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因为这一旅途危险重重且归期不定,如果他们没有成年的儿子,就需要一个“被信赖的” (“trusted”) 成年男性朋友来代替他们持有他们的领地、财产等。虽然他们的妻子也可行使一定的权力,但囿于时代背景,当时的女性仍然不被允许行使完全的权力,财产和领地仍然需要男性控制。因此,出征人的领地和财产仍需要一个“被信赖的”成年男性朋友管理。[6]
在此背景下,即将出征的领主和骑士就会将他们的领地和财产以 “ad opus” 的方式转到这名“被信赖的”成年男性朋友名下,他会为出征人的利益而持有这些领地和财产。如果出征人平安回家,他会把领地和财产归还给出征人;如果出征人没有回来,他必须使用这些领地和财产产生的收入照顾出征人的家庭,并在出征人的儿子成年后把领地和财产转让给他。这一安排就是信托的雏形。[7]
此后的《末日审判书》(Domesday Book,拉丁语:Liber de Wintonia)也记载了以“ad opus”方式持有土地的案例。这种制度也曾应用于教会等宗教组织。当时的一些教会在长年的经营中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为了避免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和忌惮,常常将其持有的土地等财产交由其他人,让其为教会之利益而持有。[8]
综上所述,从法律构造来看,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形式的用益权制度的核心在于:财产(通常为土地)虽然形式上转让给受托人(如甲将土地转让给乙),但实质上乙必须为指定受益人(可能是转让人甲或第三方丙)的利益而持有和管理该财产。这种“名义所有权”与“实质受益权”相分离的法律设计,构成了信托制度最原始的表现形态。[9]
二、 香港信托法要点概述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8条明确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这一规定从宪法层面确保了香港原有法律体系的延续性。
在此法律框架下,普通法系中的信托法律制度得以完整保留,具体包括:(1)判例法体系:香港法院继续遵循英国普通法传统中积累的大量信托判例;(2)成文法规范:以香港法例第29章《受托人条例》(Trustee Ordinance, Cap. 29)为核心,该条例系统规定了受托人的权利义务、信托财产的管理规则等基本制度,构成香港信托法律体系的主要成文法依据。
(一)《受托人条例》
1. 受托人的权力与责任
《受托人条例》第三条规定,《受托人条例》赋予受托人的权力是任何成文法则或设立信托的文书(Trust Instrument)赋予的权力外的附加权力。如果设立信托的文书 (Trust Instrument) 没有进行明确的排除,受托人就拥有《受托人条例》中赋予的所有权力。[10]《受托人条例》赋予受托人的权力主要包括一般的投资、售卖财产、给予收据、投保、个人受托人转信托、收取酬金等等。[11]
因此,在实践中确定受托人的权力和义务时,一般首先查阅设立信托的文书,其次查阅《受托人条例》,如《受托人条例》中赋予的权力与信托文书的规定不抵触,则受托人就拥有该权力。如果设立信托的文书、《受托人条例》以及其他成文法中没有具体的规定,则可以参考判例法以确定受托人的权力和义务。
此外,《受托人条例》还规定了受托人应负的法定谨慎责任,规定受托人须采取合理的谨慎态度,及运用合理的技巧行使受托人权力。在衡量受托人是否达到合理标准时,法院会考虑受托人是否具有或使人认为其具有任何特别知识或经验。[12]
2. 受托人的任命与罢免
关于受托人的任命与罢免安排,一般首先依照设立信托的文书的规定。此外,《受托人条例》也赋予了法庭以及既有受托人任命新受托人和任命新受托人以取代原有受托人的权力。
《受托人条例》第42(1)条规定:“凡适宜委任新受托人,亦发觉如无法院协助,作出委任并不适宜、会有困难或并不切实可行,则法院可作出命令,委任一名或多于一名新受托人以替代任何在任受托人,或作为额外受托人……”
此外,如设立信托的文书中并未排除既有受托人任命新受托人的权力,则受托人可根据《受托人条例》第37(1)条赋予的权力在一定条件下委任新受托人或额外受托人。该条规定:“凡任何由法院或其他人委任的原有或替代的受托人去世、不在香港超过12个月、意欲获得解除交托予他或授予他的所有或任何信托或权力、拒绝或不适合作为该等信托或权力的受托人、无行为能力作为受托人或不足21岁,则在符合本条例就受托人数目而施加的限制下 ——
(a) 设立信托的文书(如有的话)为新受托人的委任而提名的人;或
(b) 如并无获提名的人,或获提名的人不能及不愿意作为受托人,则在当其时的尚存或留任受托人,或最后尚存或留任受托人的遗产代理人,
可用书面委任一名或多于一名其他人(不论是否身为行使权力的人)作为受讬人,以代替上述已去世、不在香港、意欲获得解除、拒绝作为受讬人、不适合或无行为能力作为受讬人或不足21岁的受讬人。”
同时,由上述第37条允许任命新的受托人以取代未满21岁的受托人的规定也可看出,一般情况下信托的受托人应年满21岁。[13]此外,《无争议遗嘱认证规则》和《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也分别规定,一般情况下21岁以下的人不可被授予遗产管理书 (letters of administration) 或遗嘱认证书 (probate),该等管理遗产或执行遗嘱的权力会被授予其父母、监护人或近亲等人代为行使,直至其年满21岁为止。[14]
(二)归复信托 (Resulting Trust)
信托不仅可以通过委托人主动、明示设立,还可能经过法庭的认定默示地成立。在财产的法定所有权由原所有人转移给其他人,但根据衡平法的法律原则,原所有人仍然保有该财产的实益权益的情况下,法院可认定归复信托成立,将该财产返还给原所有人。[15]
归复信托可再细分为推定归复信托(presumed resulting trust)和自动归复信托(automatic resulting trust)两个大类,其应用场景有所不同。
1. 推定归复信托
当原所有人将自己持有的财产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新所有人,但并无证据显示原所有人有意将该财产赠予新所有人的情况下,因为衡平法推定原物主总是想要保留其在财产上的权益或要求返还财产,[16]那么法院会根据推定归复信托的法律原则,判定该财产须返还给原所有人。
在此类案件中,转让人需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包括证明受让人未就该财产转移支付合理对价,或者证明双方不存在赠与的法律合意。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会重点考察交易对价(consideration)的公允性、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以及财产转移的具体背景等因素。当这些要件得到满足时,衡平法将拟制成立归复信托关系,使受让人承担返还财产的义务,从而确保财产权益回归至转让人。
比如在Hodgson v Marks [17]一案中,原告人Hodgson太太年事已高,与一名房客Evans一同居住,并将房产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了他,并未收取任何对价。Evans将房产出售给了本案的被告人Marks。Hodgson太太主张Evans仅是以信托形式为她持有房产,并主张自己在房产上的权益。
法庭认定Evans是以推定归复信托的形式为Hodgson太太持有该房产,因为Hodgson太太在将房产转移给Evans时并未收取任何对价。此外,Marks的确是注意到了Hodgson太太居住在房产里,但并未就此提出疑问,因此Marks的衡平法权益存在瑕疵,法院判决Marks以推定归复信托的形式为Hodgson太太持有该房产并让她在该房产中居住直到她去世。
2. 自动归复信托
当原所有人尝试将自己持有的财产通过各种方式转移给新所有人,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完全的转移,在这种情况下法院会通过自动归复信托将财产返还给原所有人。[18]比如原所有人设立信托,试图将其名下的财产转移给受托人,但因信托不符合法律要求不能有效设立,这时法院可以通过自动归复信托的法律原则将财产返还给原所有人。
比如在Boyce v Boyce [19] 一案中,一位父亲在遗嘱中说明想把自己所有的房产分别留给自己的两个女儿,Maria和Charlotte,并且由Maria选择自己想要的房产,剩下的房产将分给Charlotte。但Maria还没作出选择就去世了,随后父亲也去世了。
法院认定因为父亲设立的信托因实益权益的范畴模糊而无效,所有的房产通过自动归复信托成为父亲遗产的一部分。
(三)法律构定信托 (Constructive Trust)
在特定情况下,法院也会通过“构定”信托的方式以防止欺诈行为或有违诚信和良知的行为。或者在案情事实显示当事方之间默认存在设立信托的共识但双方没有明确表示设立信托的情况下,法院也会通过“构定”信托的方式使案件得到公平的解决。这种信托被称为法律构定信托。其中,在后一种情况,即当事方之间默认存在设立信托的共识情况下,法庭构定的信托也称为共同意向构定信托 (common intention constructive trust)。
比如在Bannister v Bannister [20]一案中,Bannister夫人将其拥有的2座小屋中的一座出售给其姐妹的丈夫Bannister先生,双方同意出售之后Bannister夫人仍然可以居住在出售的小屋中。但Bannister先生随后向法庭起诉,希望将Bannister夫人赶出该小屋并取得小屋的管有权。
法院认定,虽然双方之间有明示的合约以及信托约定,但并不符合涉及土地的信托的法定形式,因而信托不成立;然而法院可以通过法律构定信托的方式执行他们之间有瑕疵的信托,以驳回Bannister先生不诚信且违反良知的诉求。
法律构定信托与前文所述的归复信托的认定情况基础有许多的相似之处。如上文举例的Hodgson v Marks 和Bannister v Bannister两个案子似乎都既可以解读为归复信托也可以解读为法律构定信托,但法院仅选择了其中一种说法。现今的香港法庭会逐个分析每个案子不同的案情事实并将其归类为其中一类信托。因为在传统上,香港法庭一般认为归复信托和法律构定信托是制度性的 (institutional) 而非救济性的 (remedial),意为只有在事实案情符合制度规定的标准和条件时,法庭才可认定归复信托或法律构定信托存在。[21]
三、 信托法在香港法律范畴内的应用
(一)遗产规划与继承
在遗产规划与继承中,遗嘱信托(Testamentary Trust)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法律工具,指的是在遗嘱中设立信托,即在遗嘱中写明委托人去世时将其全部或特定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依委托人的意愿管理遗产,将遗产或管理遗产获得的收益在特定时间向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进行分配。[22]
相较于传统意义的遗嘱而言,遗嘱信托能够给予遗产受益人更安全的生活与教育保障,灵活实现复杂的资产分配方案,其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代为管理遗产,实现保值增值
当遗产受益人尚不具备管理遗产的专业能力的情况下,遗嘱信托能够选定合适的受托人代其管理并运营遗产,使遗产保值增值,实现家族财富传承并持续性增长;
2. 保障受益人权益
当遗产受益人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如未成年),遗嘱信托可以指定受托人,以保障受益人在遗产中的权益,避免遗产被他人不当控制或使用;
3. 灵活分配,避免遗产挥霍浪费
在适用传统遗嘱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遗产受益人会在立遗嘱人去世后一次性分得遗产,且可以自由处置,有可能造成遗产的挥霍和浪费。而通过遗嘱信托,立遗嘱人可以设定更灵活的分配条件,比如可以设定在受益人不同人生阶段实现教育、就业、婚姻、生育等目标后享受相应的财产利益。[23]
(二)婚姻财产与离婚分配
1. 明示信托作为财产保护工具的作用
信托法在香港婚姻财产分配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些高净值人士会通过信托为自己或为子女隔离资产,避免离婚时被分割。信托在这一方面主要具有如下优势:
(1) 隔离财产
信托资产将被独立划分出来,在财产持有人(通常为父母)过世时不会被作为遗产处理分割,能避免家族财产违背持有者的意愿通过婚姻转移到他人手中。此外,因受益人(通常为子女)对信托资产拥有受益权但不拥有所有权,在子女离婚时,信托资产一般不会被认定为婚姻资产而参与分割。
(2) 避免婚内财产混同
信托所取得的投资收益属于信托,独立于受益人,与婚姻进行过程中新产生的财产分离,有效避免财产混同问题。
(3) 为配偶设置有条件的受益人地位
可通过信托附加条件指定配偶或子女的配偶为受益人,只要不离婚,其配偶就可以从信托中取得受益权;如果离婚,其原配偶就会因失去配偶身份而失去信托的受益权。由此,可让自己或子女在婚姻中掌握一定的主动权、维持婚姻稳定。[24]
虽然如此,在离婚处理财产分配时,法院仍然有权审查信托设立的真实意图。如果法院认定信托仅为规避婚姻责任而设,则可能判令信托无效或调整其受益权。
在英国判例Charman v Charman [25]中,英国法院判定,如婚姻财产涉及信托,即使该信托是合法合规成立的有效信托,也可能被视作婚姻财产进行分割。此外,当部分潜在婚姻财产由一些离岸公司持有时,法院可能“刺破公司面纱”(pierce the corporate veil),以认定该公司实际是为离婚配偶一方以信托形式持有财产。
随后,香港法院也采用了类似的处理方式。在Kan Lai Kwan v Otto Poon &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td [26]一案中,法庭虽未直接认定该案涉及的信托是虚假信托,但由于委托人对信托资产拥有很大限度的控制权和支配权,法庭最终判定该信托属于婚姻财产。
2. 归复信托和法律构定信托在婚姻案件中的应用
归复信托和法律构定信托通常被法庭用于处理婚姻财产(尤其是房产)登记的法定所有人和实际贡献人不符的情况,以及用于纠正不公平的财产安排。典型的情况包括父母资助夫妻双方购房的情况、夫妻双方联名购房但一方贡献较多(如支付首期和月供)的情况,以及夫妻一方虽未直接出资购房,但长期承担家庭开支并照顾子女使另一方能专注事业积累财富的情况等。在这些情况下,举证责任落在试图通过归复信托或法律构定信托申索自己在婚姻财产中的权益的一方身上(以下称为“原告方”,被申索的一方成为“被告方”)。[27]
在审查原告方提交的证据时,法庭调查的起点是要看究竟是否存在“基于各方的共同意向而产生的构定信托”,其中有以下几个重点:
(1) 原告方若要成功举证,必须证明(i) 虽然物业以被告方的名义购入,但双方的共同意向是:原告方才是物业的实质业主;(ii) 原告方依赖此共同意向,带来对其不利的改变;(iii) 容许被告方依赖物业的法定业权,并不公道;
(2) 要确定是否存在“共同意向”,所采用的是客观标准。除非任何一方指称这“共同意向”在后期有所改变,否则,需要考虑的只是在购入物业的当时,各方的“共同意向”是什么;
(3) 法庭首先要查看的是各方是否对物业的实质业权进行过明显的讨论而达成了协议或共识。若没有此等证据,则可以根据各方的行为,推断各方的共同意向是什么。[28]
四、 案例分析
为更具体地说明信托法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法院对信托的认定,笔者将以此前经手的一个案件为例进行具体阐述。
(一)事实背景
1. 当事各方及关系
原告人与被告人是离异夫妇关系。原告人是男方,被告人是女方,两人于2008年结婚,但婚姻关系短暂,仅同居约2个月,于2013年离婚。
2. 争议问题
(1) 联名账户中的270万港元:原告人将其从父母遗产中获得的资金存入与被告人联名持有的联名账户,后被被告人转至其个人账户,争议焦点在于该笔资金的实益权益归属问题。
(2) 房产A:原为原告人单独持有的房产,后转为与被告人联名共有(joint tenancy),被告人主张为赠与,原告人主张该转让是在自己受到不当影响(undue influence)的情况下进行的;
(3) 房产B:原为原告人的婚前财产,2010年转让至被告人名下,被告人主张为购买,对价为170万港元,原告人同样主张该转让是在自己受到不当影响的情况下进行的。
(4) 离婚协议(Consent Order):2013年双方达成离婚协议,双方同意原告方支付给被告人3万港元作为最终财务和解金,双方放弃其他财产主张。争议焦点在于离婚协议是否能禁止原告人对被告人提出进一步财产主张。
3. 原审法院的判决
(1) 联名账户中的270万港元:法庭认定被告人以信托形式为原告人持有该笔资金,但基于离婚协议的“最终和解”条款,原告人无权再向被告人主张;
(2) 房产A和房产B:法庭驳回原告人主张,认定房产A的转让无不当影响,且原告人签署文件时知情;房产B的转让同样无不当影响,且原告人收到部分对价。
(3) 离婚协议:法庭认定离婚协议构成“争议禁反言”(issue estoppel),即禁止原告人重新主张资产。
4. 上诉法院的判决
(1) 离婚协议:推翻原审法院的认定,离婚协议不禁止原告人在后续诉讼中向被告人追索联名账户中的270万港元。
理由:离婚协议中,双方确认财务安排为“完全和最终解决”(full and final settlement),并放弃进一步主张,但协议未明确列出具体财产归属,仅笼统提及“双方财产及婚姻期间衍生的财产”,未明确解决资产的实益所有权(beneficial ownership)问题,因此原告人的信托主张未被“必要解决”(not necessarily compromised)。
(2) 联名账户中的270万港元:推翻原审法院的认定,认定归复信托关系成立,被告人应返还该笔资金(扣除已用于原告人支出的部分)。
理由:首先因为原告人经济情况一般,无理由将全部资金赠予被告人;其次,联名账户的设立目的是为了方便被告人管理原告人的租金和支出,其中的资金并非赠予原告人;第三,被告人未能证明联名账户中的资金属于“无条件赠与”,且后续该联名账户中的资金曾被用于支付原告人的医疗和法律费用,进一步支持了归复信托的成立。
(3) 房产A和房产B:维持原审法院的认定。
5. 总体评述
本案是一起涉及婚姻财产纠纷的典型案例,上诉法院最终部分支持了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判决体现了法院对婚姻财产关系中归复信托认定、不当影响证明标准以及对价条款效力的严格审查,同时明确了离婚协议与民事财产主张的界限。
五、 总结
信托制度作为普通法系中的重要法律工具,在香港的法律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遗产规划、婚姻财产分配到家族财富管理,信托的应用场景广泛且灵活,能够有效保障受益人权益、实现资产保值增值,并在复杂的经济关系中维护公平与诚信。香港独特的法律环境,包括《受托人条例》的完善规定和丰富的判例法,为信托的设立与执行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出,法院在处理信托相关争议时,注重审查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严格遵循衡平法的原则,以确保正义的实现。未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信托在香港的法律实践中的应用将继续深化,为个人和家族财富管理提供更多可能性。
脚注:
[1] David Hayton (General Editor) with Paul Matthews and Charles Mitchell, Underhill and Hayton, Law Relating to Trusts and Trustees (London: LexisNexis Butterworths, 17th ed., 2007).
[2] 第三条,海牙公约《信托的法律适用及其承认公约》
[3] Steven Gallagher, Equity and trusts in Hong Kong: doctrine, remedies and institutions, Sweet & Maxwell/Thomson Reuters, 2017.
[3] 同3
[4] 同3
[5] 同3
[6] 同3
[7] 同3
[8] 同3
[9] 同3
[10] 第3条,《受托人条例》(香港法例第29章)
[11] 第3部,《受托人条例》(香港法例第29章)
[12] 第3A条,《受托人条例》(香港法例第29章)
[13] 第37条、第38条,《受托人条例》(香港法例第29章)
[14] 第31条,《无争议遗嘱认证规则》(香港法例第10A章); 第39条,《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香港法例第10章)
[15] Steven Gallagher, Equity and trusts in Hong Kong: doctrine, remedies and institutions, Sweet & Maxwell/Thomson Reuters, 2017.[16] Dyer v Dyer (1788) 2 Cox Eq Cas 92
[17] Hodgson v Marks [1971] Ch 892
[18] Steven Gallagher, Equity and trusts in Hong Kong: doctrine, remedies and institutions, Sweet & Maxwell/Thomson Reuters, 2017.
[19] Boyce v Boyce (1849) 60 ER 959
[20] Bannister v Bannister [1948] 2 All ER 133
[21] Steven Gallagher, Equity and trusts in Hong Kong: doctrine, remedies and institutions, Sweet & Maxwell/Thomson Reuters, 2017.
[22] 冯慧,吴寒:家族财富传承方式之介绍——遗嘱信托,2020,https://www.chinalawinsight.com/2020/07/articles/dispute-resolution/%E5%AE%B6%E6%97%8F%E8%B4%A2%E5%AF%8C%E4%BC%A0%E6%89%BF%E6%96%B9%E5%BC%8F%E4%B9%8B%E4%BB%8B%E7%BB%8D-%E9%81%97%E5%98%B1%E4%BF%A1%E6%89%98/#_ftn1
[23] 同13
[24] 方燕玲:避開子女婚姻風險的家族信託,https://www.succession99.com/News_info.aspx?ID=6105
[25] Charman v Charman [2007] EWCA Civ 503
[26] Kan Lai Kwan v Otto Poon & HSBC International Trustee Ltd [2014] HKCFA 66
[27] 葉鳳蓮對黃燕珍(HCA 2293/2004);判案書日期18/12/2009 第18段
[28] Liu Wai Keung v. Liu Wai Man [2013] 5 HKLRD 9, para 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