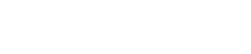企业国有资产交易规范化的新里程碑:继承、超越与监管并行
发布时间:2025-03-13
文 | 张从轩 汇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引言
中国国有企业资产交易监管体系的完善是深化国企改革、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抓手。随着2025年2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操作规则》(以下简称“新操作规则”)的出台,原2009年《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操作规则》(以下简称“旧操作规则”)正式废止,并与2016年《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监督管理办法》)共同构建起国有资产交易的制度框架。本文从新操作规则的继承性、超越性以及其与《监督管理办法》并行的监管实践价值,揭示其作为国有资产交易领域制度深化的里程碑意义。
一、继承:制度延续性与稳定性的实践优化
新操作规则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旧操作规则实践基础上进行技术性优化与体系化整合,体现了制度延续性和改革递进性。
(一)基础原则的延续
旧操作规则确立的“等价有偿、公开公平公正、市场竞争”三大原则,仍然构成新操作规则的核心框架。例如,新操作规则第三条要求企业国有资产交易“遵循等价有偿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在信息披露、竞价程序等环节进一步细化实操标准。这种继承性保障了市场交易行为的稳定性,避免因制度断层引发合规风险。
(二)程序流程的承袭:从决策到履约的标准化路径
交易流程的“决策-信息披露-受让方确认-交易签约-资金结算-变更登记”主线未改变。例如,新旧操作规则均要求转让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提交产权交易机构审核;均要求信息披露公告期需达到法定最低时限,并明确延长公告期的条件(第十二条对比旧操作规则第十七条)。这种路径的延续性为企业适应新操作规则减少了制度转换成本。
(三)风险防控机制的保留:交易保证金与合规性管控
新操作规则延续了交易保证金的设置(第十一条)、合同禁止回购条款(第三十条)等风险防控措施。同时,继续强化交易各方材料真实性承诺(第八十六条)、保密义务(第九十三条)以及争议解决机制(第九十四条),确保交易过程的合法合规性。
(四)交易程序的精细化优化
在具体操作层面,新操作规则对产权转让流程进行了显著优化:
决策前置合规性增强:新增“转让方需制定产权转让方案,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形成书面决议”的要求,相较旧操作规则仅强调“履行决策和批准程序”,进一步明确企业内部治理责任。
预披露--信息披露机制强化:旧操作规则要求“通过产权交易机构发布信息”,新操作规则则细化预披露制度,明确“转让导致实际控制权转移的需提前预披露”,提升交易透明度。
中介服务规范化:新操作规则第八条要求转让方“委托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开展审计和资产评估”,弥补了旧操作规则对第三方机构资质审查的疏漏,降低评估舞弊风险。
整体而言,新操作规则在整体框架上的继承性体现了政策连贯性,避免了对市场既有规则的冲击,为后续改革创新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二、超越:交易规则的创新与突破
新操作规则的制度设计突破了传统国有产权交易框架,对旧制度施行十余年中的痛点问题,结合新时代国资监管需求,通过四方面革新实现了创新与突破。
(一)交易范畴的拓展
新操作规则第二条明确其适用对象为“依法设立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的企业国有资产交易行为”,相较旧操作规则仅针对“企业国有产权转让”,覆盖范围从单一的产权转让扩展至企业增资、资产转让等多类型交易,同时与《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定义的企业产权转让、增资、重大资产转让三大行为形成精准对应。
新操作规则的出台,还填补了相应制度的空白,形成了覆盖“产权-资本-资产”的多维度交易体系,更符合国企混改需求。
(二)流程优化的精细化:弹性机制与操作标准并举
新操作规则在信息披露、竞价方式、资金结算等环节引入多项创新。
信息披露的灵活分级:采取预披露与正式披露相结合(第九条、第四十七条),允许因不可抗力补充披露并延长公告期(第十五条、第五十三条),形成动态调整机制;明确标的企业控制权转移时必须预披露(第九条),进一步防范突击交易风险。
分阶段降价的透明管理:转让底价调整增设阶梯降价要求(第十六条),规定新底价低于评估值90%需批准,遏制恶意压价行为。
网络竞价顺序提前:新操作规则将竞价方式中的网络竞价提前到第一位,体现了鼓励竞价方式向网络化转型(第二十五条),有效推动了交易效率的提升。
交易资金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新操作规则第三十二条要求**“交易资金必须通过产权交易机构指定账户结算”,特殊情况需提供转让方批准文件及付款凭证**(第三十二条第二款)。旧操作规则虽提及账户独立(旧第三十八条),但未明确场外结算的例外程序。新规堵截了资金“体外循环”漏洞,确保资金流向可追溯。
分期付款的利息与担保限制:新操作规则第三十五条规定,分期付款的首付比例不低于30%,并首次提出延期利息不得低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付款期限压缩至1年内(旧操作规则未设利息与期限上限)。
(三)合规边界的确立:从模糊裁量到明确清单管理
新操作规则通过“负面清单”明确禁止性行为,如禁止交易合同约定股权回购、利益补偿条款(第三十条、第六十九条);严格限制增资企业与股东间资金支持(第六十九条);对企业控制权转移后的字号使用权作出限制(第八十八条),有效封堵了灰色操作空间。
(四)主体责任的分工细化:产权交易机构与监管机构协作
新操作规则强化产权交易机构的中立监督职能,明确其对交易材料的审核义务(第十条、第二十条)、竞价过程的组织协调责任(第二十四条至第二十六条),并建立档案留存制度(第九十一条),形成交易机构与国资监管机构的协同监管网络。
新操作规则通过覆盖范围的扩展、程序的精准设计与责任主体的明晰,构建了更为立体的交易管控体系,体现了制度设计从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型。
三、与《监督管理办法》的协同效应
新操作规则与《监督管理办法》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形成“战略-战术”或“实体法+程序法”的互补结构,前者侧重操作流程,后者立足监管权限,共同构建闭环管理体系。
(一)制度定位的分工
《监督管理办法》作为顶层设计文件,明确了企业产权转让、增资及资产转让的审批权限(第七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八条)、非公开协议转让的适用条件(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五条)等宏观规则;新操作规则则聚焦操作层面,细化交易各环节的具体要求,例如规定资产评估完成后“投资方遴选前”必须完成核准或备案程序(第四十六条),是对《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增资程序的具体落地。
(二)程序节点与监管链条的衔接性
二者在关键程序节点上形成强制约束链。例如,《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转让底价低于评估值90%需批准,新操作规则第十六条进一步明确批准主体为“转让行为批准单位”;《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要求增资信息披露不少于40个工作日,新操作规则第五十一条将披露方式拆解为“预披露+正式披露”累计40日,确保程序合法性的同时兼顾效率。
此外,两套规则在监管节点上也实现了动态联动。比如,事前审批联动:《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要求国资监管机构“审核批准产权转让”,而新操作规则第七条明确转让方需“履行批准程序”,形成行政审核与流程执行的双重校验。再如,新操作规则要求产权交易机构制定服务收费标准并公开(第九十二条),对接的是《监督管理办法》第五十四条“交易机构条件”中的透明度的监管要求。
新操作规则与《监督管理办法》形成“上位法统筹方向-实施细则保障落地”的配合关系,共同构成国有资产交易“全周期监管链条”。新操作规则还通过嵌入更多量化指标与执行细则,成为《监督管理办法》落地的重要工具。
四、新操作规则的制度价值与挑战
新操作规则作为国有资产交易领域承前启后的关键制度设计,其在优化交易流程、强化监管效能的同时,亦成为了新一轮国资改革深化的重要支点。然而,任何制度革新均需在实践检验中不断调适。新规则所构建的规范化体系能否真正落地生根,既取决于其自身价值的释放程度,亦需直面外部环境中的现实挑战。
(一)价值突破:三位一体的规范化
新操作规则通过“继承旧制-衔接监管-嵌入技术”的路径,实现三重规范化:
流程规范化:从松散的程序要求转向标准化操作模块;
权责规范化:明确转让方、交易机构、监管部门的义务边界;
数据规范化:依托信息化手段建立统一交易数据池。
(二)潜在挑战与改进空间
交易机构能力差异:部分地方产权交易机构可能难以满足“网络竞价条件”等硬件要求。
非公开协议交易监管盲区:虽已规定“按国资监管规定执行”,但需防范隐形利益输送;
跨境交易细则缺位:第六十五条“境外国有企业交易比照执行”,仍需出台配套解释。
补充对策建议:
针对交易机构能力差异,建议国资委建立“标准化交易平台模组”,供地方机构低成本接入;
对非公开协议交易,可借鉴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披露规则,强制公开交易双方最终实控人信息;
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制定境外交易细则,明确离岸SPV(特殊目的公司)纳入监管的范围。
结语
《企业国有资产交易操作规则》的出台,标志着国有资产交易从“分散管理”向“体系化治理”的跃升。其既承袭了旧操作规则的市场化基因,又通过规则细化与技术革新,成为《监督管理办法》的“行动指南”。二者的协同效应,将为国有资产的高效流转与安全护航提供双重保障,亦为后续深化国企改革奠定制度基石。展望未来,随着数字监管工具的深化应用与跨境交易规则的完善,国有资产交易有望进一步融入全球要素市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