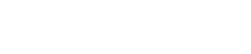公有领域认定与著作权保护
发布时间:2025-03-04
文 | 赵晋 汇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近期,河北沧州某食品公司在其产品及包装袋上使用了沧州当地知名文化地标和建筑地标的沧州铁狮子和沧州清风楼的外形线条图装饰元素引发网友广泛关注。类似使用知名地标建筑线条图或轮廓图等用作产品包装或广告宣传的设计元素在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该案例中,原告创作了《沧州行迹沧州地标建筑符号》系列美术作品,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一系列文创和包装作品。原告据此向法院主张被告侵权并提出经济赔偿。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沧州铁狮子、清风楼,均为沧州的建筑地标和文化地标,是沧州的标志性建筑,属于公有领域的作品。从被告提供的沧州铁狮子和沧州清风楼的实拍图片以及从前述实拍图片中提取的沧州铁狮子和沧州清风楼的线条图来看,原告主张保护的权利客体本身来源于公有领域,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据此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著作权侵权诉讼实务中,以涉案作品应属于公有领域作品进行抗辩在不侵权抗辩事由中较为常见,特别是一些美术作品、文学作品设计中类似抗辩比较集中。本文就著作权视野中公有领域的界定做一些介绍讨论。
一.典型案例确立的公有领域抗辩裁判规则
提到公有领域抗辩适用的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2006年度十大知识产权民事案例之一即火柴棍小人案【 (2005)高民终字第538号】是不得不提及的。
原告朱某自2000年4月起至2001年9月,陆续创作完成含有“火柴棍小人”形象的《独孤求败》、《过关斩将》、《小小特警》等作品,并进行了著作权登记,上述作品的人物形象均为“火柴棍小人”形象。2003年10月,某知名体育品牌公司作为广告主,通过活动及宣传推广其新产品,并在相关网站、地铁站台及电视上发布广告,广告中使用了“黑棍小人”形象。
原告为此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根据判决书的描述,将“火柴棍小人”形象和“黑棍小人”形象比较,两者基本构成要素完全一样,“黑棍小人”形象特征与“火柴棍小人”形象的基本特征相同,二者的头部均为黑色圆球体且没有面孔,二者身体的躯干、四肢和足部均由黑色线条构成,二者黑色线条的粗细、厚重、圆润程度以及给人的整体美感程度基本相似。但是“黑棍小人”的头和身体呈分离状;小人的四肢呈拉长状,这与“火柴棍小人”形象不同。整体上,“火柴棍小人”形象给人的感觉是线条比较硬朗,“黑棍小人”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比较柔和。
被告在本案中提出了公有领域作品抗辩,并提交了《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跳舞的小人”形象图案、韦伯斯特大学词典中“线条小人”的释义及古代壁画、上海市交通标志等一系列证据,证明公有领域中涉案小人形象的既有存在。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书的披露,在二审开庭审理过程中,原告代理人在回答有关原告“主张权利的火柴棍小人形象的概念和范围是什么”的问题时陈述:“在本案中我们主张的范围是静态的动漫人物形象。”但原告没有明确指出被告发布的包含“黑棍小人”形象的广告中“黑棍小人”的哪一个静态形象与其“火柴棍小人”形象完全相同或基本相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原告代理人的陈述,原告主张的是静态的“火柴棍小人”形象的著作权,因此,本案审理的范围在于静态的“火柴棍小人”形象是否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黑棍小人”形象是否侵犯了“火柴棍小人”静态形象的著作权。根据现有证据,在“火柴棍小人”和“黑棍小人”形象出现之前,即已出现以圆球表示头部,以线条表示躯干和四肢的创作人物形象的方法和人物形象,但是从“火柴棍小人”的创作过程及其表达形式看,该形象确实包含有原告的选择、判断,具有他本人的个性,原告力图通过该形象表达他的思想,因此,“火柴棍小人”形象具有独创性,符合作品的构成条件,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由于用“圆形表示人的头部,以直线表示其他部位”方法创作的小人形象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任何人均可以以此为基础创作小人形象。另一方面,“火柴棍小人”形象的独创性程度并不高。因此,对“火柴棍小人”形象不能给予过高的保护,同时应将公有领域的部分排除出保护范围之外。将“火柴棍小人”形象和“黑棍小人”形象进行对比,二者有相同之处,但相同部分主要存在于已进入公有领域、不应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部分,其差异部分恰恰体现了各自创作者的独立创作,因此,不能认定“黑棍小人”形象使用了“火柴棍小人”形象的独创性劳动。“黑棍小人”形象未侵犯原告“火柴棍小人”形象的著作权,被告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该案距今已有近二十年,但该案中确定的裁判规则及其示范效应却一直被司法实践不断运用并验证。该案所体现的公有领域的认证界定正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剖析该案,我们可以总结出:关于某种表达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并不影响以此为基础进行的创作可以构成作品的认定,只是在侵权判断时,需确认被诉侵权作品与权利人作品存在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的表达部分是否来源于有明确指向内容的公有领域,并据此来认定公有领域合法来源抗辩是否成立。
二.公有领域抗辩的具体适用
《著作权法》本身并没有关于公有领域的明文规定,但部分条款却因需要保护公共利益,确保公众得以自由使用公有领域资源而有所设置。比如第五条规定的本法不适用于:(一)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其他具有立法、行政、司法性质的文件,及其官方正式译文;(二)单纯事实消息;(三)历法、通用数表、通用表格和公式。
进入到司法实践中,对于公有领域的讨论就非常直接和必要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发布的《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七章抗辩事由的审查中直接明文列举了公有领域抗辩,即被告能够举证证明被诉侵权作品与原告作品存在相同或者实质性相似的表达部分来源于公有领域的,可以认定公有领域合法来源抗辩成立。
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全面加强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中就提到,在知识产权审判中,必须妥善处理激励创新与维护公平竞争的关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必须依据现行法律,不应超越法律规定的标准。凡属于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成果,必须坚决保护,以此鼓励创新;凡不属于知识产权范围的信息,均属于公有领域,应允许自由利用和自由竞争。在涉及知识产权与公有领域界限模糊的法律领域,必须在激励创新与鼓励自由竞争之间搞好利益平衡,划定和适用的法律界限应当有利于营造宽松的创新环境,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应当意识到:任何一部新作品的诞生,既存在作者独立创作的内容,也必然包含从先前已有已知或公知领域中移植、汲取的非原创部分。百分之百的原创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部分或多或少的非原创内容,逐渐积累进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成为公有领域的公众资源。作者的创作活动得到财产激励和合理回报后,对作品的支配与利用就应当转化为全社会共享的公共财富。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外著作权法会普遍为著作权设置一个权利期限的根本原因。
因此,就著作权法法益中公共领域的概念,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主要指权利保护期届满后的作品,这些作品随着保护期限的届满,不再受著作权保护,从而成为公众可以自由使用的公共资源。而从广义角度而言,公有领域的范围并不仅限于此,还应包括前文提到的因缺乏“独创性”等要素而无法获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以及已经存在的众所周知的已知表达或创作方法等。而究其本质,公有领域抗辩,并非是要否定作者的权利,而是要限制权利的滥用。在具体的个案审理中,被告对于公有领域的抗辩,并不影响对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作品是否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作品的认定。而抗辩一方,必须以充分的证据来陈述公有领域的具体表达内容指向,最终由法庭进行边界划分。
三、对创作者的合规提示
我们在鼓励创作者原创的同时,也要提醒创作者,在创作时应尽到审核义务,避免侵犯他人已经在先发表的成果,尤其是现如今已全面迈入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在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不断汲取“数字养分”,但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也是基于公有领域中海量的数据信息,通过捕捉融合与深度学习而后得来。因此,创作者在利用这些资源时,应充分尽到审核、注意义务,尊重公有领域的边界,明确区分公有领域素材与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只有在尊重知识产权、合理利用公有领域资源的基础上,创作者才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充分发挥其创造力,推动文化产业的进一步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