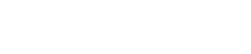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正当目的
发布时间:2024-12-30
文 | 王丹妮 冯娇阳 汇业律师事务所
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是公司财务信息的重要载体,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权利对公司治理、股东权益保护都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享有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权利,旨在保障股东对公司经营状况的了解和监督。但为了防止股东滥用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该条款同时对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作出了限制性规定。股东行使这一权利时,需满足前置程序的书面形式、目的正当的形式外观要件,公司也可抗辩股东查阅的实质目的具有不正当性。
一、设置查阅目的的合理性
正当目的指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或监督公司经营管理,例如了解公司财务状况以评估股权价值、监督公司管理层是否存在不当行为等,而非出于恶意或其他不正当动机,如恶意竞争、敲诈勒索、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损害公司声誉、损害公司利益等。在知情权诉讼中,如果法院认定股东查阅会计凭证具有不正当目的,将导致股东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公司可以基于保护商业秘密、维护公司利益等合理理由,拒绝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请求。
股东知情权,包括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权利,旨在防止信息不对称,调和股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股东与公司经营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同时也需考虑公司自主经营权和商业秘密的保护。股东知情权的理论基础包括公司治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前者强调股东通过知情权参与公司治理,后者则关注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代理问题。与此同时,公司信息保护,尤其是商业秘密的保护,是防止股东滥用知情权损害公司利益的关键。例如,商业秘密的泄露可能削弱公司的竞争优势,因此需要预防性保护以防止潜在的威胁性侵害。
股东知情权的行使需要在保护股东权益和维护公司信息安全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点:股东有权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但需受到限制,以防权利滥用,保护公司的经营秩序及商业秘密。这涉及到股东说明查阅理由的责任、公司证明不正当目的的举证责任,以及对商业秘密的预防性保护措施。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既要保障股东的监督效能,也要防止对公司利益的潜在损害,会基于个案的案情判断,要求股东说明查阅的理由,并要求公司举证证明股东查阅具有不正当目的,以此达到权利义务的平衡。
二、正当目的认定标准
知情权的行使是有条件的,必须出于正当目的并在合理的时间和地点行使。正当目的限制是为了防止股东滥用查阅权,损害公司利益。股东的查阅请求不能出于不正当目的,如妨碍公司正常运营、泄露商业秘密或进行竞业活动。
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理由通常包括:(1)行使股东监督权,确保公司管理层的透明度和合规经营;(2)发现潜在的不法行为,如财务异常或长期财务造假,股东需要会计凭证以核实账簿信息的真实性;(3)在遭受经营者或大股东压制的情况下,股东可能需要查阅会计资料以保护自身权益。
考虑到现实中公司财务不规范、财务造假事件频发,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财务管理问题,股东仅能查阅会计报告可能不足以保障其知情权。因此,当股东能提出合理怀疑,如管理层的不当行为或财务报表的不真实性,应当允许其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以实现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平衡。在利益衡量的过程中,股东举证证明其前置程序满足书面形式、目的正当的形式外观要件即可。而公司拒绝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则应由公司举证证明股东查阅的实质目的具有不正当性。司法实践中,法院通常会综合考虑股东的申请理由、公司经营状况、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等因素,来认定股东查阅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的正当性。
引入“正当目的“的目标是通过限制股东无序的查账请求来求得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但由于立法用语的高度抽象,“正当目的“的裁判基准迟迟不能明确,使得司法在平衡股东与公司的利益面前进退失据。[1]正当目的的实体认定基准无法回避,尚需将法院实践积累的裁决经验上升为正式规范文件的恰当表达,提供更明确的裁判规则。例如,典型案例中涉及“同业竞争“情形下股东的不正当目的的认定,法院认为:“不能简单以股东经营公司同类业务或者在其他同类业务公司中担任董事或则高级管理人员就认定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而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而应判定是否形成实质的竞争关系,比如在客户、项目招投标、经营地域等方面存在竞争。“[2]
曾有学者研究过公司在知情权诉讼中使用不正当目的抗辩的情况:在股东知情权诉讼中,“不正当目的“的抗辩是公司可能使用的策略。早期的法律实践对此标准的界定较为模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对于“不正当目的“情形进行了细化,通过列举四类不当目的,为不当目的的含义提供了指导。但如果公司只是提出抗辩,而没有提供具体证据,通常得不到法院支持。法院更倾向于要求提供具体证据来证明股东的请求确实存在不正当目的。总体而言,提出不正当目的抗辩的案件占所有案件的30.57%。在其中列举的三类具体的不正当目的中,股东从事与公司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是最常见的抗辩理由,很少有案例中提及的抗辩是为他人提供信息而查阅、在过去三年为他人提供信息而查阅。[3]
三、正当目的的比较法规定
美国的司法管辖区在股东知情权诉讼的证明标准上存在分歧。以特拉华州为代表的司法管辖区采用可信基础标准,要求有外部证据以推断出公司的不当行为,而不仅仅是怀疑、好奇或与管理层的分歧。少数司法管辖区则要求股东只需证明存在理性信念,即管理层可能存在不当管理。理性信念符合逻辑即可,不必参考外部证据。
特拉华州最高法院拒绝接受理性信念的标准,担心过于宽松的标准会导致滥诉。相反观点认为,多项因素反驳了特拉华州最高法院这一假设,同时法院低估了采用可信基础的阻碍效果。实际上,可信基础在阻止诉讼方面的作用比预想的要大得多。研究发现,虽然理性信念下的滥诉和可信基础上阻碍诉讼的问题都存在,但后者的程度超过了前者。调查结果通过逻辑回归分析展示,当潜在原告对管理不善只有轻微怀疑时,理性信念导致起诉的概率增加了17-52%。这体现了理性信念的诱导效应。当潜在原告强烈怀疑但不确定管理不善是否发生时,可信基础降低了56-75%的诉讼概率。两组数据显示威慑效应超过了诱导效应。因此,有学者建议法院在知情权诉讼中采用理性信念,同时对给公司带来沉重负担的检查项目实施成本转移(Cost-Shifting)。成本转移是指在股东查阅公司材料时,法院可以要求股东承担部分或全部的查阅成本。这种做法旨在防止股东进行无目的的“钓鱼式“调查或恶意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如果发现符合可信基础标准的证据,股东则可以得到成本的补偿。[4]
印第安纳州上诉法院在Charles Hegewald Co. v. State ex rel. Hegewald案中对正当目的进行了论证。该案案情为,某公司股东去世后,其遗产管理人Mena C. Hegewald要求公司将会计账簿交给其聘请的会计师查阅。Hegewald在提出查阅要求时说,她的目的是要了解股票价值以便计算遗产税。被告公司没有拒绝让Hegewald亲自查阅会计账簿,但拒绝让她聘请会计师查阅。法院认为,只有在事实表明原告有明确的合法权利获得所要求的救济,而被告有明确义务去履行原告的主张的情况下,才会签发强制令。如果没有责令原告确定其股权价值的任何法律责任,而由公职人员承担确认股权价值的责任,并且公职人员不受原告的调查和结论的约束,则仅仅凭借原告希望了解股权价值以便缴纳遗产税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公司负有义务将账簿提交给原告聘请的会计师。原告希望了解股权价值,并不能使原告享有查阅会计账簿的权利。除非股东权利在不查阅的情况下可能受到严重损害,否则不授予股东查阅公司账簿的权利。[5]
这样的结论似乎将原告的查阅权建立在原告负有查明事实的法律义务之上,该案例与美国法的主流观点并不一致。如果税务估价师的估价有误,原告应该能够对其估价提出质疑。要做到这一点,原告必须了解事实。原告并没有因为投机目的或为满足无聊的好奇心而行使查阅权,而是为了合法的目的寻求信息。[6]
在实践中,有些法院使用联邦民事诉讼程序(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Rule 26(b)(2)(B)来确定成本高昂的检查是否有合理原因。Rule 26(b)(2)(B)是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的发现规则,旨在处理电子存储信息的可发现性问题。这条规则规定,如果恢复数据会带来“不合理的负担或成本“,那么这些数据可能是不可发现的。这条规则规定了在某些情况下法院可以限制或排除发现(discovery)的情况,特别是当获取电子存储信息会带来不合理的负担或费用时。Rule 26(b)(1)概述了法院在决定是否批准发现请求时应考虑的一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诉讼中问题的重要性、争议金额、各方获取信息的能力、资源对比、发现信息对解决争议的重要性,以及负担或成本是否超过了其可能带来的益处。
股东可以通过证明“合理原因“来推翻数据不可发现这一假设。法院在确定是否存在“合理原因“时,会考虑请求的特定性、其他更容易访问来源的信息量、未能提供似乎存在但已无法从更易访问来源获取的相关信息等因素。此外,请求方愿意分担或承担查阅成本也可能被法院考虑在内。
当股东基于合理信念请求检查时,如果第一层级的文件(如正式董事会决议、会议记录等)未能满足“可信基础“标准,法院有权拒绝进一步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要求股东承担检查成本,或者允许检查继续进行但将成本部分或全部转移给股东。如果检查揭示了与“可信基础“标准相符的证据,股东将得到成本的补偿。例如,在Woods v. Sahara Enterprises, Inc.和KT 4 Partners LLC v. Palantir Technologies, Inc.案中,法院允许股东检查某些文件,但同时要求股东承担检查成本。[7]
四、司法案例
1、海南省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四起保护中小投资者典型案例之三:邵某与某建筑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典型意义】
实践中,中小股东通常不参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股东和管理人员之间信息不对称。在此背景下,法律通过赋予股东知情权,特别是能够反映公司经营状况与财务信息的会计账簿查阅权,是保障中小股东权利得以有效行使的必要前提和手段,也是监督公司运行的重要措施。本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进行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对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举证证明其前置程序满足书面形式、目的正当的形式外观要件即可。而公司拒绝股东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则应由公司举证证明股东查阅的实质目的具有不正当性。本案通过举证能力、举证目的的考量合理分配举证责任,保护了中小股东的权益。
2、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15起保护中小投资者典型案例之六:黄某与厦门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同业竞争“情形下股东不正当目的的认定
【典型意义】
现实中股东经营公司同类业务或者在其他同类业务公司中担任董事或则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非常普遍。如果仅以股东经营公司同类业务或者在其他同类业务公司中担任董事或则高级管理人员就认定股东与公司存在“同业竞争“而认定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而拒绝股东行使股东知情权,再加上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的优势,中小股东的权益就更加难以保护了。对于“同业竞争“的情形中认定是否构成不正当目的的关键在于判定是否形成实质的竞争关系,如果股东经营公司同类业务或者在其他同类业务公司中担任董事或则高级管理人员并不一定形成实质的竞争关系。例如在本案中,虽然原告黄某设立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根据企业登记的经营范围与被告厦门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近似,但上海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地域在上海,被告厦门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地域在厦门,同时被告也未提供证据证明两家公司在客户、项目招投标等方面存在竞争关系,而只是单纯的依靠企业登记的经营范围来认为原告有不正当目的而拒绝股东黄某行使股东知情权,明显缺乏说服力。
由于中小股东天然的“弱势地位,“审判实践中请求行使股东知情权的案件的主体基本是中小股东。“同业竞争“情形下股东的不正当目的的认定,不能简单以股东经营公司同类业务或者在其他同类业务公司中担任董事或则高级管理人员就认定股东存在不正当目的而拒绝股东行使知情权,而应判定是否形成实质的竞争关系,比如在客户、项目招投标、经营地域等方面存在竞争。
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发布中小股东权利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三:原告曾某诉被告甲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公司对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存在不正当目的之抗辩应承担举证责任
【典型意义】
股东知情权是法律赋予股东通过查阅公司文件和账簿等有关公司经营、管理、人事、财务等相关资料,了解公司运营状况的权利,是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享有其他权利的基础。会计账簿是公司最为重要的经营材料之一,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时存在一定的边界和限制。当公司认为股东行使对会计账簿的知情权存在不正当目的时,可以拒绝股东进行查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八条对于“不正当目的“情形进行了细化。其中规定,除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股东另有约定外,股东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公司主营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业务的可以被认定为存在不正当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关于举证责任的一般规定,公司主张股东查阅会计账簿存在不正当目的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甲公司提交的公示信息仅可以证明曾某所任职的乙公司在经营范围上与甲公司有部分重合,但甲公司并未提交其他证据证明乙公司经营的业务与其有实质性竞争关系。因此,仅凭两公司经营范围的重合,不足以认定曾某查阅会计账簿存在不正当目的。因此,法院对于甲公司主张曾某查阅会计账簿存在不正当目的的答辩意见不予采纳,对于曾某在本案中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和保护。
4、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2021年度中小投资者保护十大典型案例之四:赵某与南召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股东申请查阅会计账簿存在不正当目的,公司有权拒绝其查阅要求
【典型意义】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的固有权利和法定权利,但应依法行使。股东提出查阅会计账簿的请求应基于正当、善意的目的,并与其作为股东的身份或利益直接相关。如果股东违反诚实信用和善意原则,出于开展同业竞争、获取商业秘密等损害公司经营等不正当目的申请查阅会计账簿,则公司有权拒绝其查阅要求。
脚注
[1] 李建伟:《股东知情权诉讼研究》,《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
[2]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15起保护中小投资者典型案例之六:黄某与厦门某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同业竞争“情形下股东不正当目的的认定。
[3] 黄辉:《<公司法>修订背景下的股东知情权制度检讨:比较与实证的视角》,《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3期。
[4] Lynn Bai, Shareholder Inspection Rights: From Credible Basis to Rational Belief, 10 Emory Corp. Governance & Accountability Rev. 193 (2023).
[5] Charles Hegewald Co. v. State ex rel. Hegewald (Sup. Ct. of Ind. Oct. 27,1925) 149 N. E. 170.
[6] McNutt, Paul V. (1926) "Stockholder's Rights to Inspect Corporate Books and Records," Indiana Law Journal: Vol. 1: Iss. 1, Article 4.
[7] Lynn Bai, Shareholder Inspection Rights: From Credible Basis to Rational Belief, 10 Emory Corp. Governance & Accountability Rev. 193 (2023).